□黄超鹏
读过一篇汕头作家的文章,将我的家乡三饶比作“幽幻之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三饶人,我觉得他的描述流于表象,不尽准确。
小时候,从我能记事时起,我从父辈们口中得知关于三饶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它曾经是饶平的老县城所在,县治史长达475年,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可惜在1953年1月县城迁往黄冈镇后,三饶的经济和发展曾一度停滞不前。那时,村里的大人们聚在一起喝功夫茶聊天,谈到一前一后的落差,铮铮铁骨的潮汕硬汉瞬间化身成为令人讨厌的祥林嫂——不是絮絮叨叨地回忆旧日时光,就是张牙舞爪地假设畅想:要是县城没有搬走的话,我们就如何如何……刺鼻的烟气与蒸腾水气弥漫间,我曾恍惚以为,是一群白头宫女在抱怨唐玄宗的薄情。
等到上学后也一样,校园里随处可见地充斥着不安与焦虑。老师们头顶着“第一中学”的陈旧招牌,一边不时发出“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一边想尽法子申请调到山外边的世界去。县城“第一”的名号形同虚实,能争第一的学生早已跑到县城的重点中学和潮州的名校就读。有能力逃离的人想出去,没机会的人早早地放弃,故事的结局仿佛早已注定。我们越不争气,内心便会愈发忧虑。
我工作后,还是毫无例外地感觉有种无形压力如影随形。三饶妇女们教育子女的方法似乎都如出一辙:女孩子长大嫁人,要当个好媳妇,任劳任怨,三从四德,当好男人背后坚实的后盾;男孩子要刻苦耐劳,敢拼敢闯,凭借智慧与干劲和无尽的冒险精神,打拼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家当。男人要炼钢,要顶得住万千压力。但当你小有成就,母亲会告诉你隔壁家的谁又赚了多少个亿;而女人得化水,懂得包容隐忍,还得学会绕指柔。但当你自以为踏入“合格线”,母亲会猛然告诉你隔壁家的媳妇又生了二孩。
那位汕头作家记忆中,三饶与灯火幽幻的城隍庙,和自己差点被父母送到三饶当养子的遭遇画上等号,因此他称三饶为“幽幻之城”。我的记忆中,三饶则是与忧心忡忡、患得患失的年少记忆扯上关系,折射出一些“忧患”的影像。想必不管我如何细述,终会有其他三饶人跳出来说,你说的不对。毕竟一千个读者读《红楼梦》,脑子里就会有一千个贾宝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心中那个宝玉才是最贴近曹雪芹笔下那个。
不过,如果一定要我想一个别人无法吹毛求疵的词,来形容我心目中的三饶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词,就叫做——家乡。

46745f18-22c3-49e3-9e2c-2ccd35396dc3.jpg)
30c91afa-8f0b-45c0-b98d-ac624d87364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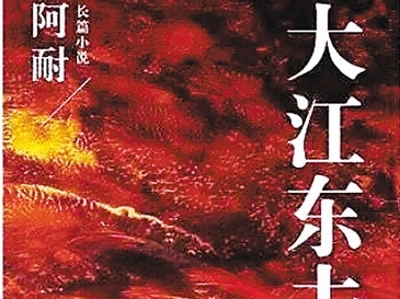
ca265386-3601-487f-96fc-100f4e33c6cb.jpg)

71dca782-dd8d-4de4-bef4-36084d2f2789.jpg)

2774291a-ce46-430a-8200-1e71448a81ff3a48dd31-877e-4271-a5b6-2d18689ab513.jpg)
003ee3c0-809f-4330-a116-85450f42073d.jpeg)
3563d80b-44e0-4f9b-b346-138f5b514ba67b306214-8446-49cf-8a66-2fb3f838b48c.jpeg)
d73caaa4-3541-47e7-b115-c19162d23d06.jpeg)
1b7a053b-7136-4bcc-9812-7bea0c8e33c3.jpeg)
14a130f0-893b-449a-af97-1967189309d4.png)

7261a65e-9b75-4247-a9fc-234847894959.jpg)
9b5f8c7a-1d5c-4350-afe2-ea8e433684bc.jpg)
26952bd6-2597-4c16-a60e-169d480909fc.jpg)
747f9ee0-d489-4228-b6e2-f933e8101483.jpg)
18db3b10-7737-453f-ae9e-757923646269.jpg)
029d5d05-5fda-4d4d-b83a-96e21974c238.jpg)
61b03c71-17c4-4bbd-a0c8-3a2dd1c8d709.jpg)
fbd00b46-9d45-4b8c-8e2b-29db750413f9.jpg)
70312a3b-301a-47b9-bd14-7d249005a65f.jpg)
e3ef20fe-57ed-45ab-b8cd-4cb7216a311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