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致敬辞
肖复兴以烟火万象的真情书写,在当代散文创作中自成一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创作力旺盛,写作类型广泛,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流通机制的变迁。其平实隽永的文字,历经时间的淘洗,给一代又一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燕都百记》在延续细腻笔触的同时,走向简约和克制,选取100处作者在北京城内曾经生活、流连过的地方,记录老北京的前世今生,生动再现隐藏在这些地名背后的人与事、感动与温情。于平凡世相中,描摹人生命运,留下时代印记。文字豁达洒脱,从容自在,治愈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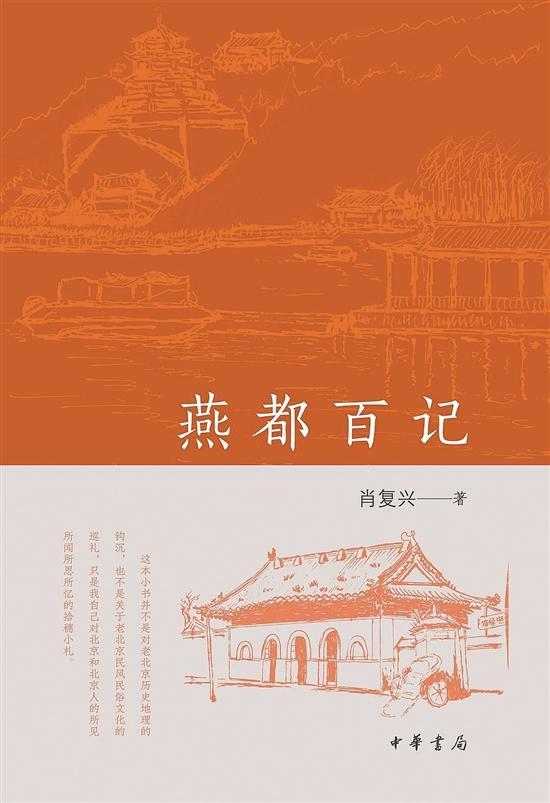
感言
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肖复兴
52年前,也就是1971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里喂猪,冬天大雪封门,无处可去,我陆续写了10篇散文不知该往何处寄。我就挑选了其中一篇寄给了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可巧,当时他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赋闲在家,看了我这篇单薄的文章,立刻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他在信中说,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
于是我把剩下的其他九篇散文都寄给了他,他一一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而且不是一般的修改,是逐字逐句地修改,其中有一篇,因为改动特别大,他怕我看不太清楚,就重新抄改了一遍再寄给我。所以,那个冬天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
我之所以在今天这样隆重的盛典上回忆起这桩往事,是因为如果没有叶至善这样细致、耐心的帮助、鼓励、扶持,就没有我今天写作的结果。
我从那一天,一直走到今天,在文学的小路上得到了无数像叶至善这样的前辈、编辑和朋友们的帮助、鼓励和扶持。可以说,他们的名字隐在了作者的背后,像风,看不见,却推动作者前行,我非常感谢他们。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访谈
“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
羊城晚报:您写了20年北京,北京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和生命而言,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肖复兴:我今年76岁,除了到北大荒的6年,其余70年都生活在北京。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南、前门一带、前门西侧老街,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粤东会馆,我对它们最熟悉。在2003年的冬天,我偶然路过那里,重走故地,发现那里还是我儿时见到的模样,感到格外亲切。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似乎扑面而来。
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写作之间的关系。
我在一座三进的清代老四合院住了21年。比起以后更长的年头,人生最初这21年似乎留给人的记忆更深。老街坊大多还在,见到我很高兴,纷纷走出屋,问这问那。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曾经住在这里的往事,一下子都涌到眼前。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写这里呢?这里我熟悉呀,这里有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记忆,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是和北京这座老城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呀!
羊城晚报:书中选取北京的100个地点书写,有怎样的选择标准?
肖复兴:这100个地点,都是和我有关系的,包括我曾经住过、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一定要有我、和我认识或交往过的人,要有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有我、人、事这三要素。
有了这样的“三合一”,才会是我所记录的老北京。尽管不是北京全景,但却是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和别人眼里、和以前书里并不完全一样的老北京。
羊城晚报:书中有不少您手绘的街头巷角插图。除了写作,您对音乐、绘画也颇有研究。穿行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肖复兴:我正在读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的新书《摹仿叙事学》,借用他的说法,传统文学是言说叙事,戏剧影视是摹仿叙事。他援引亚里士多德“双管箫乐和竖琴乐”的理论,进一步说明颜色和姿态等形式作为摹仿手段实现叙事意图,都在无形中拓宽了文学仅靠文字的叙事策略。
我喜欢音乐和画画,尽管都不入流,但这样的爱好无疑帮助我拓宽了对传统文学的认知,也拓宽一些文学书写的边界。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可以彼此借鉴,相互受益。而且,在这样的相互纠缠和交融中,独有其乐。
羊城晚报:现在越来越多作家为城市写史立传,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您会考虑为北京写一部传记吗?
肖复兴:为城市写传当然是好事,但我不大赞成一窝蜂都去为自己的城市匆促写传。我觉得当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只有历史材料的堆砌和排列组合,并不是传记的真正写法。
当年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也只囿于历史、地理两个方面,并没有写成或叫作《北平传》。我自己更不会去写《北京传》,我不具备这个能力。
避免重复,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
羊城晚报:北大荒也是您创作中的“魂牵梦绕之地”。在您心中,真实的北大荒是怎样的、在您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肖复兴:我虽然写过北大荒,但那只是我所认知的北大荒,是我青春时节经历的北大荒,我最近有本新书,名字就叫《我的北大荒》。因为我只在那里生活过6年,没有经历过它的以前和现在,对它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北大荒,只是和我们自己的青春、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和那片土地有关。
如果问北大荒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或我们的北大荒的意义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在那个不可或缺的断代史中,我们是亲历者、书写者、言说者,反思者、批判者。
羊城晚报:您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的亲历者之一。您如何回忆80年代文学?今天的文学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肖复兴:80年代的文学,值得纪念,尽管不成熟,却有难得的激情和直面现实、人性及自我的那一份真实与真诚。如今的文学,虽在技术层面和数量上有发展,但那两方面却不如以前。由于文学书写者的地位与姿态心态的变化,这是必然的。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力的?现在还每天都坚持写作吗?
肖复兴:一般没有事,我每天上午坚持写点儿东西,下午出门,闲逛,有时到公园画画,尽管画得拙劣,却特别煞有介事地画速写。
我觉得画活物和人的速写最有意思,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颇有成就感。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这也是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吧。尽量避免重复,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儿。
主要在写之前,一定要多想想。一是所写的内容要想明白,是不是有点新意;二是所写的方式要想清楚,比如开头结尾还有没有更好更新的想法,尤其是结尾。没想好,别动笔。
羊城晚报:您有不少文章入选语文教材,对于孩子的阅读,您有什么建议?
肖复兴:对于孩子的阅读,我一般建议:一、太长的不读,孩子如今课程压力大没那么多时间;二、太老的不读;三、太时髦的不读。
读什么?一是读他们喜欢的,感兴趣的;二是好文章要反复多读几遍。桑塔格说:“最好的阅读方式是重读。”这样的经验对孩子一样合适。三是可以抄一点儿,只读书,不抄书,学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养成抄书然后再延伸到记笔记的好习惯,一辈子受益。
苦难中的诗意是散文最可贵的品格
羊城晚报:在您的整个创作谱系中,散文居于怎样的地位?您曾提到散文难写,这个“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肖复兴:散文易写难工。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小说、戏剧一直被认为是“小道”,而集部的诗和文,才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散文,是一切文体的基础,又是一切文体的塔尖。只是如今我们的作家以为长篇小说是塔尖,是文学的大道和正宗,散文只是散步的小径。
按照布罗茨基所说:“艺术就其天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有等级划分的。在这个等级之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但按照诗人阿赫玛托娃所说,散文则是高于诗的。她说:“走进散文时似乎有一种亵渎感,或者对于我意味着少有的内心平衡。”她还说,散文对于她“永远是一种诱惑与秘密”。
似乎在我们的作家与诗人中,少有像阿赫玛托娃这种对于散文创作怀有虔诚与敬畏之感的作者。想想自己,惭愧得很,尽管常与散文为伍,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少有散文写作时独有的那种“诱惑与秘密”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的散文向来注重平凡生活、普通人群的温情故事。一个作家该如何练就观察生活,把普通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
肖复兴:散文写作,当然有多种写法。我赞同孙犁先生所说的:“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这里所说的“无关紧要”和“人不经心”,指小事的两个方面:“人不经心”,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即熟视无睹;“无关紧要”,是看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即见而无感。
我一直喜欢散文。读中学时,现代作家的散文,喜欢冰心和萧红;当代作家里我喜欢韩少华和何为。年老之后,喜欢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些作家的散文,共同的特点,都是书写普通生活,并从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温馨、温情、温暖,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当然,生活常会充溢一些不如意、坎坷、痛苦,甚至血淋淋。我自身的经历,也逃脱不出这样的命运跌宕。即使如此,生活中也不乏温馨、温情、温暖的诗意。苦难中的诗意,让我们面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信心,以及忍耐和等待的韧性。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可贵的性格,也是散文最可贵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我喜欢这样的散文,希望自己也写这样的散文。
个人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各类杂书两百余部。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