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致敬辞
青春,是“80后”青年作家周嘉宁一直书写和探索的主题。她笔调轻柔,在不着痕迹中为读者构建了“一块干净明亮的精神世界”。
《浪的景观》也不例外,它是周嘉宁的进阶之作,三个青春故事、一群青年朋友,呈现的却是世纪之交大横断面的生命景观。
她以扎实、生动、精确、节制的叙事,雕刻出了时代和青年群体的“一部分”灵魂,典范性地构筑出当代城市小说的筋骨和血肉,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新时代城市变迁与个人史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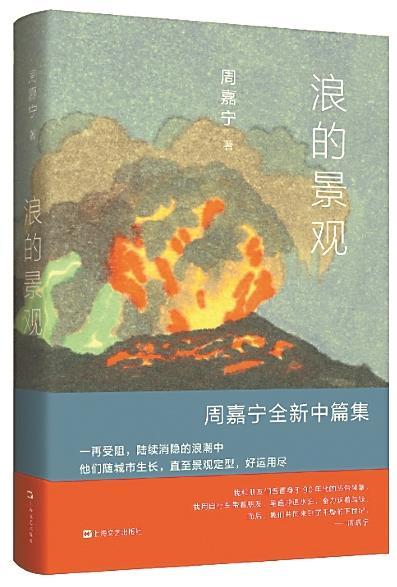
感言
写作为我构建虚实之间的通道——周嘉宁
对于我来说,已经度过了真正意义上的青年时代,但是能够获得“年度新锐文学”这个奖项,从某种意义上鼓励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学徒的心态。
《浪的景观》这部小说集创作于2018年至2021年,是我对世纪初的上海所经历过的那段青年文化复兴时期的沉淀与回望。在时代的浪潮中,年轻人随城市共同生长,直至景观定型,所形成的共振却延续至今。
我非常感谢我的主人公,陪伴我度过四年的时光。在这四年当中,我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描述和记录各种形态的“浪”。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主人公已经坐上了皮划艇划到了河的对岸。
他们蹚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那里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和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到结实的地面。很多手电的光照在水里,照在树叶上,但无论如何都不再能照到他们的身上。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始终维持着我写作,这个问题在回答了很多次以后,我才真正发现,其实并不是别的东西在维持着我的写作,而是写作始终提供给我动力,让我得以维持我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得以不断在现实和虚构世界之间一再构建通道。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访谈
试图提供尽量多的视角
羊城晚报:将《再见日食》《浪的景观》《明日派对》三个故事集纳在一本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周嘉宁:因为在2018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我只写了这三个中篇,放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我上一本书《基本美》在2018年出版,在写书中最后一篇同名小说《基本美》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写作的语言风格有一些变化。
中篇小说集《浪的景观》我觉得是对这种变化进行巩固,探讨的问题也是从《基本美》开始的,它们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一直到写完最后一篇《明日派对》,可能差不多是我一个写作阶段的结束。那时我思考的一些问题,包括世纪之交,以及全球化对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影响等,在这三个中篇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之后我要开始其他内容题材的写作了。
羊城晚报:以“浪的景观”为书名,是否代表了对同名小说《浪的景观》的偏爱?
周嘉宁:如果从小说本身来说,第一篇《再见日食》和第二篇《浪的景观》我都挺喜欢的,但是《浪的景观》的意象总体上更能够表达我这三篇小说想传递的内容。
羊城晚报:“浪的景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有什么隐喻?
周嘉宁:我并没有想去隐喻什么,写作的时候脑海当中出现的那些场景是非常直觉性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看过某一波“浪潮”的起伏,我周围有一些胆大的人,有一些幸运的人,有一些在关键时刻做出很好决策的人,他们捕捉到了踩上浪尖的最好时机。
然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真正踩在浪尖上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更多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真正站在“浪”里面的人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浪”的全貌,反而是一些旁观者才能看到。我在写的时候也试图提供尽量多的视角,不仅是我的视角,也希望我的小说主人公可以提供其他视角给读者。
羊城晚报:写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达,听罗大佑的演唱会、组乐队、录电台节目、卖服装……这些小说中的情节都源自您的青春经历吗?
周嘉宁:基本上都是我所看到的时代风貌,那时我周围大部分人都听电台,有很多人给电台主持人写信,还有朋友去参加电台主持人选拔比赛,等等。
包括在《浪的景观》中我写的那些外贸市场的故事,我自己肯定没有卖过衣服,但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对上海的外贸市场非常了解,经常去那边,也在那边交到一些朋友。
虽然说现在外贸市场已经拆了,也很少有人听电台了,但是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是相当珍贵的,而且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羊城晚报:三篇小说的结局似乎都不是明确的“大喜”或“大悲”,在设计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周嘉宁:我自认为这些结局都还是比较好的,是朝上走的。我不想给当中任何一个人下定论。主人公们的命运在故事结束后,仍然在虚构的世界里继续延伸下去,限定性的结尾对这些主人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个世界仍然在变化。
“未来可期”是人生的整体基调
羊城晚报:《浪的景观》呈现了世纪之交青年朋友的集体记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迷惘和成长,和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周嘉宁: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现在最年轻的那些人,他们生活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看到的东西都是社交媒体传递给我的,这里面肯定有偏差。小说主人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处于资讯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跟现在的年轻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所写的那些年轻人基本跨越了两个时代。那一代人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整个青春期都是在这种剧烈变化中度过的,他们会觉得变化是正常的,不变和稳定的东西反而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小说中的年轻人自由散漫,似乎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当下,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内卷”“内耗”严重。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思考过能为年轻读者带来什么?
周嘉宁:写的时候其实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更多的是为我的朋友而写。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我认真地看了豆瓣下面的评论,看到很多“90后”“00后”年轻读者的反馈。我能够比较清晰地感觉到,我们已经完完全全是两代人了,但好像又有一些超越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的东西,能够在小说所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里达到共振,这个是我比较开心的。
羊城晚报:上海是您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您写作的基础。如何看待城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周嘉宁: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上海的城市性格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对所虚构的世界的塑造。
我想说,每一代人跟城市的关系都不太一样。在我的青年时代,上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地,到处都在挖掘和建造。一方面非常嘈杂,对生活造成了很大不方便;另一方面,整体上来说让我觉得充满了希望,这可能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整体基调,有一种未来可期的感觉。
青春不应因“刻板印象”成为禁忌
羊城晚报:对于青春文学写作,大众似乎有一定的刻板印象。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如何避免陷入这种刻板印象中的?
周嘉宁:现在仍然有一些读者评价我的小说很“青春文学”,我也确实有想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时期。
我的想法只是继续写出好的小说,一部真正好的小说无所谓它是写青春还是不写青春。你可以避免去写青春,但青春不应该因此成为一个禁忌。因为每个时期去看待青春所提供的视角和感受都是完全不同的。
羊城晚报:2000年、2008年是您新书中的重要时间点,也是您经常写的时间点,它们有何特殊?
周嘉宁:2000年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都挺重要,它就是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
2008年也是我经常写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城市的景观面貌变化真的非常大。我在2007年来到北京,2010年离开,那三年北京城市变化的缩影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前后变成了两个不一样的时代,前面一个相对更混乱一点,很多规则还没有建立,后面那个时代突然之间各方面都在加速发展,出现很多新生事物,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它们对于我们平凡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影响非常大。
羊城晚报:《浪的景观》之后的写作计划能否分享一下?
周嘉宁:我目前在写一部长篇,写了已经有一年,但是写得很慢。相较于前几年的思考内容,我现在在思考一些别的东西,这种思考目前还处于比较混乱和挣扎的开始阶段。我希望通过这部长篇的写作能帮助我到达下一个阶段。
个人简介

周嘉宁,上海人,英语文学翻译。著有长篇小说《荒芜城》《密林中》,中短篇小说集《基本美》《浪的景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