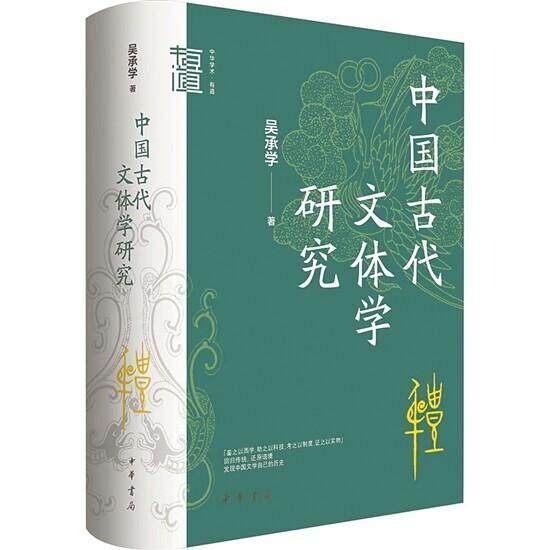
□吴承学
壹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分析报告》,“中国古代文体学”是十项入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示例”之一。
自然科学领域的“原创”,往往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人文学科则必须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古代文体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所谓“古老”,意谓它是中国本土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如果从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来看,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有意识地运用某些文体的情况。在文体的命名、称引和分类等方面,也体现了隐在的文体观念。到了汉代,已出现较为明确的文体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系统的文体学谱系已经完成建构。此后,中国文体学一直就是传统的“显学”,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以“辨体”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文体学在历代都有所发展,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传统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新的文学理论所遮蔽,被西方文学观念所主导的以虚构类、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所取代,成为被淡忘的知识谱系。
所谓“年轻”,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体学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在新世纪以来,是发展最快的学术领域之一,并逐渐建设成一门既有本土特色,又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古老的文体学重新焕发“青春”,老树重开新花。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既来自本土传统,又不等同本土传统,因为其中包含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方法、转化和阐释。东晋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说:“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此语可以借喻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
贰
中国文体学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术语很多,但只有极少数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这些概念表现了中国文学的本土性,成为其基础与核心,所以可称为中国文学的“标志性概念”。“文体学”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概念”和理论之一。中国古代文体学是典型的本土理论话语,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中国的本土性问题,可以具有超越国别文化的意义。这也是需要我们当代学者去研究,去阐释的。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之一,它既是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与基点。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的文体学体系,并非像西方那种以虚构和抒情为主的“纯文学”文体,而是在中国传统的礼乐、政治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功用基础上形成的。
在近代学术体系中,“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以西方“纯文学”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不但终隔一层,而且由于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文章”“文学”本义产生错位,容易遮蔽甚至歪曲历史真实。因为西学的强势,故其“文学”概念基本替换了中国本土的“文章”“文学”,中国文体学成为断裂的学术传统。平心而论,这种理论用于研究和指导现代文学创作,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认识传统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提高其地位,也是有益的。但无区别地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则存在很大的问题。简单地使用西方文体分类法去研究中国古代文体,会造成一些研究上的困扰。所以,从研究中国文学的角度看,强调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目的在于强调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回到中国本土文体语境,尽可能“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恢复因被套用西学而被遮蔽的中国传统文体学的光辉。
近代以来,传统文体学受到遮蔽。但是,否极泰来,否定之至,就会引起对传统的反思。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文体学的思想源头,恰恰可以追溯到近代。自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为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导夫先路。当代中国文体学崛起的意义,其本质就是传承断裂的知识传统,倡导回到中国传统文章学文体语境里研究中国文学。
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把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当作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责任,认为应该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研究,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尽可能发挥现代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学术眼光等优长,同时消解现代学人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隔膜。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的具体语境中,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揭示其原初意义;同时,以古代文体学理论的具体语境及丰富细节为基础,对其所蕴涵的现代意义,进行既符合逻辑又不悖于历史的阐释,并力图在阐释中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从衰落到复兴,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转型,这是具有深远学术史意义的。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西化倾向的调整,即向本土文体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它纠正了近代以来对于传统文体学的遮蔽,在研究规模和广度上,在理论的系统性上,都超越以往。所以,在当代学术史上,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重要性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同,中国文体学已成为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学科领域。
叁
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一批学人共同的学术理想和共同追求,我就是其中之一员。不过,我较早投入,而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攻读硕士、博士阶段中,开始关注中国文学风格学,此后在此基础上对于文体学有持续的思考。2005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提出“文体学学科”概念,认为应该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有体系的研究,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体系。同年又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一文,指出古代文体学亟需从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和视角发展为一门现代学科。2011年,我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中提出,在继承古典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并在2015年《文学评论》发表的《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中,进一步倡导建立具有现代意义与学术高度的中国文体学。
数十年来,我谨遵“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之古训,坚持在中国文体学领域耕耘,未敢放弃,《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等多种著作和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都是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
对我而言,古代文体学研究是漫长、艰辛又快乐的探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体学从解蔽到重构,从冷门到热点,从边缘到中心,成为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学学术生长点之一,并逐渐建设成为有本土特色和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数十年来,我全程参加和见证了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建设的整个进程。
肆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读到海外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大受震撼。我想,中国文体学传统有可能进行创造性转化吗?中国文体学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现在看来,这是可以肯定的。比如说,中国文体学的核心精神,便是追求“得体”,古人作文讲“得体”,做人、做事也都讲“得体”,可以说古代文体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它的核心精神已渗透到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成为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这种精神,超出了文章的范围,融进了中国人的普遍观念与日常生活。这种精神,具有超强生命力,它贯通古今,不但适合古代中国,也适合现代中国。它不但适合中国人,也可能具有某种文化普适性。所以,中国文体学的精神与理念,具有超出文体学与一般学问的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创造性转化”。
古代文体学具有当代活性,我们不能把古代文学做成脱离社会与现实、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我们要把学术需求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当然,我们不能把高雅的学术庸俗化。中国古代有些文体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产物,在现代已失去传承的意义。但是现代有很多文体,是从古代演变而来的,或者是古代文体的遗存,古今文体有相通之处。还有大量文体,比如诗、词、小说、戏曲,乃至辞赋、书牍、序跋、赠序、杂记、箴铭,在当代社会仍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与生存空间。中国古代文体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导人们进行文章写作的。文体理论研究要与文体实践相结合,要适应现实的需求。以我所熟悉的学界友人为例,如莫砺锋、曹旭、周裕锴、张海鸥、胡晓明、易闻晓、程章灿等教授,都有丰富的古代文体实践,他们一直在写古典诗文。能诗善文的年轻学者和学生更是难以枚举。国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如中山大学中文系即开设有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古代诗文写作等课程。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当代学者通过这种文体实践,可以更真切地体验古代文体学的精神。另一方面,文体实践课程也是在传播古代文体学的知识种子。
伍
文体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具有跨学科性质。我们几代学人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认识到一定要把握到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注重从文献、文体与文本中,考察文章与文心,尽可能在本土的语境里,探索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追寻中国美感与中国智慧。总结起来,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文献、文本、文体、文章这四个方面。它们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文献学,当然也和文本的变化与流动有关系。文体学与文章学或辞章学,它们之间当然有区别,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与文章学往往是浑然一体的。《文心雕龙》就是文体学与辞章学完美结合的典范。这四个“文”,当然是概括而言的,比如,文献学也包括版本目录,包括语言文字、考据之学。学术史上,有许多东西是过眼云烟,甚至是有害无益的。但无论是什么风气,最终总是难以绕过文献、文本、文体、文章这几个方面。
“文体学”是一个“广谱”问题。它不仅仅属于文学领域,凡是有文本存在的,必定有一定的形制,有“文”者必有“体”。文学、文章之外,经学、历史、宗教、文献、著述甚至科技等皆有文体。未来文体学领域必然是扩展的,文体学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分支。比如,历史文体、宗教文体、著述文体乃至科技文体等,但文学文体学仍将占主体地位。
研究中国文体学还有许多路子可走。比如,在文体与制度、文体与经学、文体与图像、文体与物质形态的关系,以及文体与文本形态流变关系、文体的实际运作、文体的运用现场等,都有无限开阔的空间。
陆
2017年11月,首届中国文体学青年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我作了题为《致新一代学人:期待超越我辈》的致辞。当年所说的青年学者即70后、80后的学者,如今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学术前沿,而且处于思想最为敏锐、精力最为充沛、最具学术创造力的黄金时代,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中坚主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超越我辈的成就。现在,大批90后、00后的学者已开始崭露头角。当年的年轻学者又面临更年轻的学者的挑战,学术史总是后浪推着前浪一步步向前的。
我往往觉得,现在年轻人学术研究的条件比我们当年要好很多,他们的学术基础与能力也要好许多,但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与生态,更为严峻,更具挑战性。现在的竞争过于激烈,年轻人的生存、发展的通道与上升空间过于狭窄和拥堵。当高层次的论文与国家级项目成为年轻教师上升的铁门槛,当极有限的学术资源面对不断增加的需求量,供求严重不对称,年轻教师和学生面对巨大压力,难免会产生一些焦虑情绪,也不易有超乎功利、从容淡定的心境去细细读书、慢慢写作。我非常关心年轻学者与学生的处境,又深感爱莫能助。我与年轻学者的处境完全不同,但学者之间是可以有共情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过于悲观,不要放弃。努力不一定有收获,但仍有希望,放弃则肯定没有机会。我总是对自己的学生说,要相信学术界仍有正气,要相信还有许多公正的学者,还有许多正派的刊物和编辑。任何时候都会有些阴暗面,但我们不要只看到或片面夸大学术界的阴暗面,消极、灰暗的心态会使人失去奋斗的动力。人首先当然要生存,但又似乎不只为了生存。优秀的年轻学者应该有更高远的自我期许和学术理想,有更宏大的学术格局,实实在在为中国学术做出贡献。学术研究不仅要在当下生存,还要活得更久,甚至在未来仍可以存活下来,“声名自传于后”,而不是“身与名俱灭”。真正的学者生于当下,活于未来。一个学者如果有一本书、一篇论文或一个观点能够传世,能为学术史贡献一砖一瓦,就可以无愧了。
我特别喜欢《中庸》的一句话,“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选取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执着地追求,永远不要放弃,这就是“诚”。《中庸》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我们中山大学的十字校训。在这段文字之后,有几句话说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一直以这段话自勉,因为我知道自己天分就是属于愚钝与柔弱的类型,所以一定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我想以这段自勉的古语和年轻学者共勉。
二十四年前,傅璇琮先生为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序,序文中有一段话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傅先生当年写序时67岁,如今,我和傅先生当年的年龄相仿。重读先生的序,更能理解他当时的语境与心境,也更能理解他所说的学者需要“傲世的气骨”,以及“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人总是会遇到困难,遇到世态炎凉,遇到委屈甚至屈辱,这也是一种人生历练。困厄之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遇到委屈与挫折,若能一笑而过,继续前行,那便成熟了。在治学路上,也不例外。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