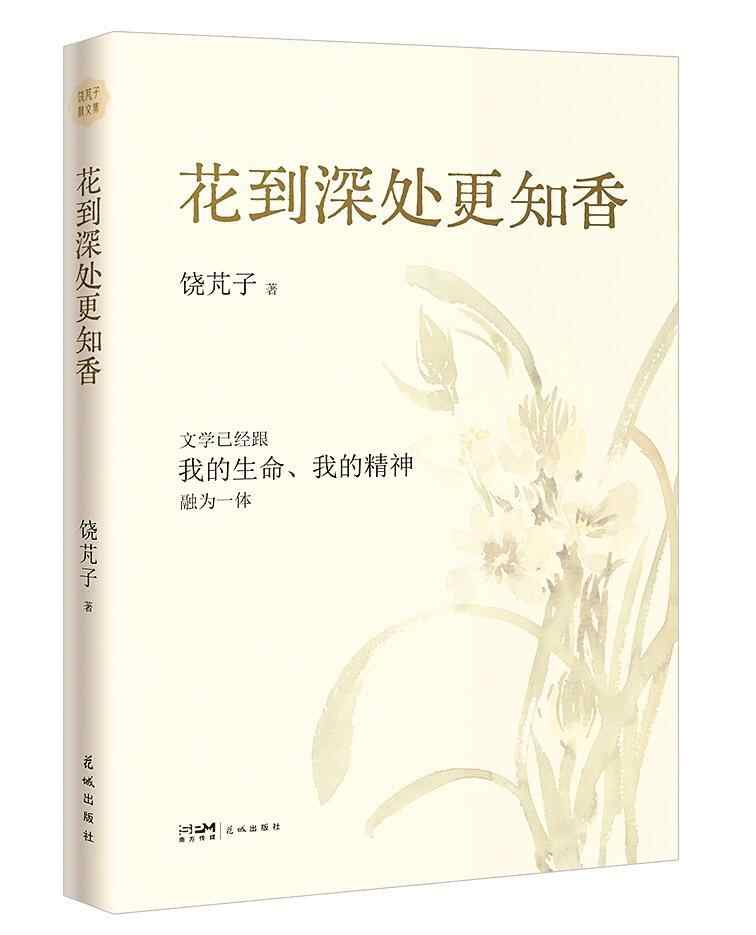
□ 项仙君
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饶芃子
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
——项仙君
有些伤痛只隐藏在心底,但总在一些日子会突然发作,恸彻心肺。
譬如在这个清明,我再也见不到的饶芃子导师。
我在2024年11月27日的微博还记录了第一时间获悉噩耗时的心情:“我最尊敬的导师,当代华文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大家,红学及张爱玲研究的领军人物,暨大最后的女先生,原副校长饶芃子教授,今早仙逝。三十年前殷殷庭训如在昨日,两月前再聆教诲话音犹温,待我如子的知遇之恩,厚学如渊的高洁人品,岂敢一日忘之!天不假年,为之奈何!敬爱的老师啊,东来原本无教义,西去从此有斯文!”
在此两月之前的教师节,我刚去祈福医院看了老师!当时她已经要依靠轮椅,口齿不清,但仍精神矍铄,反复要跟我握手,说“你样子很好”!即使知道老师已经认不出我了,还是要跟她提起我们当年的岁月,谈到刚走的乐黛云老师,说起荣耀又让她不省心的往事。护工阿姨说,每有学生来看她,她都是开心的,就算想不起来客,她的话也是讲究的。桌子上放着宾客留言簿,都是满满的祝福。握着老师不停颤动的手,心里又伤感又安定,这是塑造了我的青春的大先生啊。
在教师节或元宵节老师生日去暨南大学看望老师,已是我这么多年来的惯例,每次出来时都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些贵气。
老师是这几年身体才不行的。之前每次一进门,老师都会与我热烈拥抱,饶老师的先生吴老师在世时也会拉着我的手,说我年年来,真有心。其实毕业近二十年,中间有好几年我都没有来看望他们,觉得功名未就愧对师恩,这心理障碍是在四十岁之后才放下的。
饶老师可不看重那些,她从来就是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一谈就是个把小时。有次谈到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刚刚辞世,饶老师当即嘱咐助手发唁电给汤先生的太太乐黛云先生,口授悼词。饶老师与汤、乐两位先生的交情我是了解的,乐黛云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与饶老师一起被称为“北乐南饶”,当年我到北大参加的“首届中国青年学者比较文学研讨会”就是乐先生主持的,提交的论文还被北大学报全文刊登。我记得我发言结束后,乐先生还特地走过来祝贺,问我愿不愿意读她的博士,如愿意,她可以推荐一名学生来饶老师这儿攻读学位。
我最终因为生计所迫放弃读博,饶老师为此很遗憾。据我所知,饶老师非常敬重汤先生,汤先生也很器重她,前年她去北京开会,抽空到北大探望乐先生,汤先生当时正因病住院,听说她来了,还专门从医院出来与她见面。言谈之中,饶老师对汤先生的逝世深感悲痛。
我们学生都知道,吴老师年纪比饶老师大,但他在生活上很照顾饶老师。吴老师出身新加坡华侨世家,祖上有很大的橡胶园,并经营金银珠宝和布匹等买卖。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他大哥被日本人杀害,新加坡家产也因此败落。他年轻时勤奋好学,后考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在西北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是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虽然是理工科方面的专家,但身上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却非常浓厚,每次都与我聊得很投缘。饶老师除了与我谈近期的学术成果外,讲得最多的是她的家世:饶老师出身潮汕的诗书之家,她的外祖父戴仙俦先生是晚清秀才,后来又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回潮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家乡的语文教育事业,曾先后受聘于韩山师范、金山中学、潮安一中等学校,他不但能诗、能文,还是潮汕一带有名的书法家;父亲饶华上世纪30年代初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后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抗战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她的舅舅戴平万毕业于中山大学西语系,是作家和翻译家,与夏衍、鲁迅一起在上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弟弟曾以潮州市高考第二名成绩考上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哈尔滨,是有业绩的年轻科学家……但在“反右”和“文革”中,饶家历尽磨难。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党内右派,在个旧锡矿劳动二十年,1978年才得以平反。她和弟弟在“文革”中均受到很大的冲击。

由于家庭的影响,饶老师自幼迷恋文学,立志一辈子做学问。1987年任暨大副校长是因工作需要,上级组织决定的,开始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再三推辞。时任暨大校长梁灵光(曾任广东省省长)告诉她:这是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要她马上到任。这样她才当了两任主管文科学术和研究生的副校长。在与我聊天中,饶老师不胜感慨地说:“也许就是因为我更专注于学术,所以才能健康地活到现在。现在女儿、孙子都挺争气,学习和工作都很好,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师从饶老师之后,我才感觉以前自己矜以为傲的犬儒作风其实就像一个乡下的野孩子,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都有着致命的缺陷,宽容、大气,让心灵永远超越于日常俗事之上,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品格。的确,我从来没有见老师骂过人,连生气的时候都少,即使她提携的人后来背弃了她,她也只是一笑了之,偶尔和我发一声感叹: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在暨大的三年,老师让我们读《红楼梦》、张爱玲,背唐诗宋词,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
我曾建议老师,以后多写点散文随笔,特别是家史,因为她的家族应该是广东有代表性的诗书之家之一。老师说,这些年,她已写了系列的回忆文章,如《石头记与我》《回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旧事》《缅怀舅父戴平万》《我的父亲饶华》《告别父亲》和《我的弟弟》等,在学术工作之余,如有时间,她还会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她还说,“虽然我们经历过苦难,但这些苦难并没有在我的精神中留下残疾,我还会全心地体味在文学和学术中的乐趣”。
这是真的,不久前,暨南大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饶老师的座谈会,发行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花到深处更知香》,书的封面用的就是老师的话:“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是的,哪怕只能吃酱油拌饭,也要认真地铺上台布,这就是我领悟到的老师身上的贵气,也是一种光芒。
清明的路上滴着雨,滴着我的回忆。魂兮归来,老师啊!
(作者是南方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