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季思先生
王季思先生
1982年10月、12月,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风靡全国。十大古典悲剧包括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以及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十大喜剧则包括关汉卿的《救风尘》、白朴的《墙头马上》、王实甫的《西厢记》等,都是耳熟能详的中国古典戏曲菁华。
中国古代戏曲多以题材和行当分类,或以地域分流派,从无悲剧喜剧之分。悲剧喜剧源自古希腊,其中悲剧作家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喜剧作家则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是西方主流戏剧的源头。到了近代,中国人也开始引用欧洲的悲剧喜剧美学概念来论述中国古典戏曲,比如王国维就曾说,《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即列之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此后也有人试图将中国古典戏曲按悲剧和喜剧归类,但并无成功范例,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出版后,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喜剧归类为众多普通读者所接受,在中国戏曲发展和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季思青年时代在东南大学求学,师从著名学者吴梅,后来因校注研究王实甫《西厢记》享誉海内外,逐渐成为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名家。他从1948年开始执教于中山大学,直到1990年以84岁高龄退休。据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回忆,即使“退休以后,他依然坚持工作。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旁忙个不休”。由于思想的开放和眼界的开阔,王季思晚年的学术成就丰硕,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就包括他借鉴西方文艺美学思想梳理归类中国古典戏曲而成的这两部名著集。
王季思原来亦无悲剧喜剧概念。据易新农教授回忆,大概在1979年前后,有一次学术交流时,他告诉王先生:西方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分,中国古代戏曲也可以分悲剧和喜剧。王先生很感兴趣。恰逢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举办全国高等院校戏曲培训班,由王季思先生主持,王先生于是热情邀请易新农往该班讲学。培训班学员是各大学中文系古曲文学专业的讲师和副教授,其中南开大学的宋绵友毕业于中山大学,与易新农同班,易新农当时的职称仅是讲师。
易新农说,他的专题讲座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西方悲剧喜剧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也有人认为希腊悲剧表述的是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其次结合理论分析作家作品,重点介绍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品,如《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等。黄天骥当时是副教授,他在培训班上讲授关汉卿戏曲。易新农说,他们在培训班上的讲课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学员的广泛好评,特别是通过研讨古希腊悲喜剧,拓展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王季思先生亦受到启发,他主编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的念头正是在这次培训班中萌生的。
黄天骥教授说,王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接近,他觉得,教学相长,老专家也能从后辈身上吸取自己缺乏的东西”。他还说,王季思先生有个习惯,“他写好文章后,无论是长篇论文还是诗词杂感,总要复印出来,请自己的学生提意见”。王季思先生为十大悲剧和十大喜剧集分别作长篇前言,每篇洋洋万余字,易新农教授说,王先生写完初稿后亲自送上门来命其修正,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十八条修改意见,王先生虚怀若谷,一一接受。王先生在十大喜剧集前言的结尾谦虚地写道:“运用悲剧、喜剧的美学概念论述我国古典戏曲,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对欧洲悲剧、喜剧的理论既缺乏深入研究,对我国古典喜剧的艺术特征也探讨得不够。”然后他恳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正。
作为晚辈同事,易新农与王季思先生谊兼师友,一直保持密切交往,除问学请益外也经常嘘寒问暖,关心先生的身体和生活。1990年春天,王先生偶患小恙,易新农教授前往探视,携去《歌德谈话录》一册,推荐先生一读。此后一段时间,王先生卧病在床,以翻阅《歌德谈话录》自遣,并深有感触。几天后他赋诗一首:“一榻度昏朝,浓情闲里消。群书束高阁,清梦越重霄。魏玛何须羡,濠梁倘可邀。殷勤谢歌德,知足自逍遥。”他将这首“卧病经旬以《歌德谈话录》自遣”的五言诗抄录在宣纸短笺上,赠“新农同志存念”。所谓“殷勤谢歌德”,除了感谢这本《歌德谈话录》陪他度过病榻上的寂寞时光外,可能还有感谢包括歌德在内的西方作家、思想家对他晚年学术研究启发的意思,他也因此“知足自逍遥”。
谈起歌德和西方作家,易新农教授还想到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盲人之国》,以及他与王季思先生1979年合写的《从〈盲人之国〉想到的》一文。
威尔斯著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盲人之国》是一部短篇,讲述主人公牛奈斯误入盲人之国,该国僻处山谷,国人不相信外面世界的精彩,并与牛奈斯发生冲突的故事。小说构思奇特,寓意深刻,讽刺那些在所谓进步时代假象下的孤陋寡闻和自以为是的人。王季思读了中山大学校友陈世伊的译文,认为他与易新农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合写《从〈盲人之国〉想到的》一文,署名季思、新农,刊发在《花城》文艺丛刊第四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迎来思想解放潮流,文化界在欢呼春天来临的同时爆发“歌德与缺德”的争论。所谓“歌德”不是那位德国文豪,而是指“歌功颂德”,抨击刚刚兴起的“伤痕文学”,称“不‘歌德’者即‘缺德’”。王季思与易新农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的文章由盲人之国联系到现实,认为“打开黑暗的闸门,冲破因袭的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任务”,并称“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篇稿子又是什么缺德之作,我们也不想多作辩解,倒是想劝他读一读威尔斯的这篇作品,从误入盲人国的牛奈斯身上吸取些有益的教训”。《花城》是刚刚创刊不久的文学期刊,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反响,也有读者写信来批评作者是“缺德派”,但王季思先生不为所动,他还在《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发表《放开眼界摆脱束缚》一文,以书简的形式谈《盲人之国》,坚持自己的观点。
2020年1月,易新农教授米寿前夕,他将自己珍藏的王季思先生手泽,以及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初版本转赠笔者。惶恐之余益加感动,我想,易老师此举,也是王季思先生另一首诗中“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的意思吧。


c3814023-ffd1-4461-8994-41d945534fbd.jpg)

71c70f2c-64cf-433e-9f17-af4faf2d52fb681b65ab-23e6-4b49-9bfa-e0f5749f1a85.jpg)
8e1aa36a-f12e-4a7b-b5cc-50958b34d4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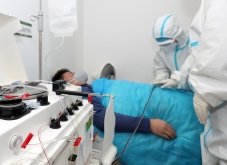



2f61fece-2717-4ced-87c1-a3028eeee116.jpg)
06fe76fb-63af-41b4-a6a3-4ad3ebd0658d.jpg)
29f2d220-c290-4895-b085-8d5e3c8d78156fe0776f-2e00-41f6-8f70-9dbb6e8adde6.jpeg)

1e165bfe-513b-446e-a1f5-097523bd91b0.jpg)
4625cbe9-9883-4c1d-b7fa-86606a2ae2ca.jpg)
67b1f3d8-37df-463c-929f-aaf84b13d13f.jpg)
8ad7350d-2248-4c1b-bd58-caafaa0eac9a.jpg)
835e9bf4-587e-4648-b89d-39abaf388f7d.jpg)
53e68a1e-b874-46f3-a6bb-11f85324afa5.jpg)
684f165c-9734-4946-978c-b8d8fd11bc7b.jpg)
3d4bbd3b-89a6-4cfe-a67c-8afc8cb3c319.jpg)
2f44a89d-f18e-43d1-805e-49bdde4a1b3e.jpg)
a1c130bd-858b-4807-9ba7-b1536bbb6f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