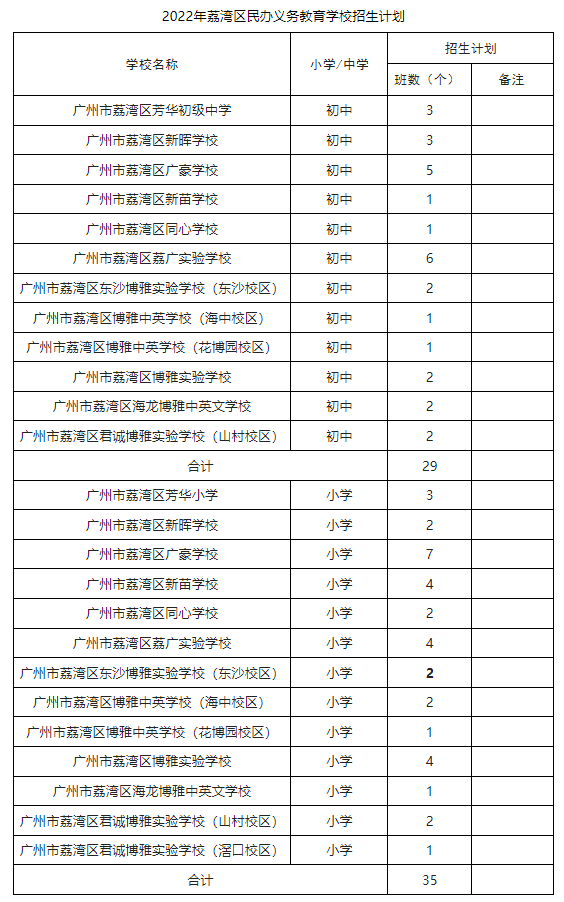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岭南文史】陈焕镛:躬行华南大地 逐梦植物王国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易芝娜 通讯员 任海虹
4月中旬,国家植物园于北京正式揭牌;而在千里之外的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也正桃李芳菲,花开满园。
清明刚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来到有“广州人的后花园”美誉的华南植物园。在园中的雕像径中,一座1:1等身大小的雕像刻画出该园的创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他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毕生在华南大地上“耕耘”,开创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新纪元,特别是为植物分类学作出奠基式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原副所长、研究员陈忠毅,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向记者介绍,在今日华南植物园科研区一隅,仍保留着陈焕镛居住过的一幢小红楼,附近还有一条小路被命名为“焕镛路”。陈院士一生采集标本达12334号,共发表了600多个植物新种与新组合、11个植物新属。华南植物园拥有的全球保存木兰科植物数量最丰富的木兰园,更是与他直接相关。园中,大叶木兰、绢毛木兰、石碌含笑以及观光木等多种木兰科植物新种,都经他定名发表。
陈焕镛院士一生守护祖国珍贵的植物、生态资源,捍卫国人的学术尊严,他的精神与实践对我们今天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启迪。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的陈焕镛半身雕像
少年立志 回国痴迷采集
1890年,陈焕镛在香港出生,1971年病逝于广州。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还有他另一尊半身雕像,那是当年由植物园同仁集资、请广东雕塑家唐大禧和唐颂武精心雕成。据说,这尊雕像与他本人酷肖,丰神俊朗、眉目棱角分明,还能看出陈焕镛的特殊血统。
陈焕镛的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清朝光绪年间曾被派驻古巴担任公使。在那里,陈言认识了古巴籍西班牙人、后来成为陈焕镛母亲的伊丽莎白。陈焕镛六七岁时曾旅居上海,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他遵循父亲遗愿,远赴美国求学。
1909年,他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安姆斯特农业学院学习树木学与昆虫学,1912年转赴纽约州立大学林学院,1915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前往哈佛大学布斯学院及阿诺德树木园学习森林学,并于1919年取得硕士学位。
陈忠毅回忆,1996年,华南植物园在40周年园庆前夕曾推出一本《陈焕镛纪念文集》,当时他是副主编之一,整理了大量与陈焕镛相关的资料文献。陈焕镛对森林保护的概念形成于美国求学期间,那时,中国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还得到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去找。由此,他心生愿望: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一生都在为之努力。
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陈焕镛放弃了留在欧美等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到海南岛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作为最早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他在海南岛五指山山区采集动植物标本数千份。当时的海南腹地还是瘴疠之地,陈焕镛常常处于疟疾的威胁中,因蚂蟥叮咬和营养不良导致浑身伤痛,甚至病倒、发烧至40℃……最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五指山山区。
保护自然 一生追求科学
从1920年开始,陈焕镛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陈焕镛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教授。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中大农学院建立起华南地区首个专业的植物标本室,继而成立中大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这便是现在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前身。
自1925年至1937年间,陈焕镛与另一位植物分类专家胡先骕合作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图谱》;创办了以“孙逸仙”命名的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山专刊》)并担任主编;他还创建了广西植物研究所,参与主持策划《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的编撰出版工作。
1956年,陈焕镛与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等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提交议案,最终获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中国至此拥有了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少年时的心愿,在他与学生、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一一实现。
1959年,70岁的陈焕镛当选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72岁时,他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全体人员大会发言中,仍要求大家“把国家任务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争取七年之内完成编辑《中国植物志》这项伟大光荣的任务,并感慨新社会“做科学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要年轻一辈好好珍惜。
科学分类 方法沿用至今
今天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是一幢新旧馆合体的五层楼建筑。总建筑面积5513平方米、满满五层楼的标本柜里,存有115万多份(涵盖48700多个物种)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8000份——新种植物被发现后,通常需要按照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来进行描述、命名。只有在和分类概念上属于近缘种的模式标本进行仔细对比比较并发表在一定专业核心刊物上,这一新种植物才算被正式发表定名。对于植物学家来说,“发表定名”新种植物是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
馆中有一批非常珍贵的标本,是当年陈焕镛与海外同行交换得来的,其中,收藏时间最早的标本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新馆里,一排排高端仓储式手摇轨道密集柜整齐排列,虽然存量庞大,却井井有条。目前,所有入库标本都已数字化,并陆续对外公开共享。标本馆高级工程师曾飞燕说,至今,所有标本仍是按当年陈焕镛留下的一套系统进行分类保存的,方便又严谨,能将所有数据都保存完好,同时也为标本室纳入国际电脑联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是在陈焕镛等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植物标本馆,终于彻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
陈焕镛也是我国最早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在这个标本馆中,至今尚存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微微泛黄的纸上装订的一枝干枯的线形叶植物,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冰川降临早已绝种。因此,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辗转磨难 护佑珍贵标本
陈焕镛深知,开展植物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标本室是不够的,所以也同时收集并进行植物种苗栽种。1989年,政协广东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史资料》第59辑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为了保存那些稀有品种植物,陈焕镛到处采集种苖,并“将采获苗木托诸广州市立植物园或农学院农场代为栽培”,建起了标本园。至抗日战争开始时,该标本园已具一定规模,可惜“在广州沦陷时为日军所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时常遭日机轰炸。1938年春,陈焕镛出钱出力,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一批重要标本、图书、仪器运至香港,自己却坚持冒险留在广州保护苗圃。后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描述,“日本人雇佣德国人搜寻藏在沙面的中国难民,他们半夜来到我藏身的地方,好在我骗过了纳粹们,后来在广州待不下去了,我就扮成苦力步行逃到了香港”。
陈德昭、黄成就编撰的《陈焕镛传记》中描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中大那一批存港标本仍遭日军扣押。1942年3月,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将植物所迁回广州,并表示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等。陈焕镛考虑再三,在声明植物所纯属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的前提下,于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路前岭南大学的校园内。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焕镛如释重负地与员工们一起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岂料此时竟有人诬告他为“文化汉奸”。当时,如许崇清、金曾澄等教育、法律界知名人士,都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同时,远在美国的梅尔教授得知情况后亦写信给美国大使馆、转交中国官方,特为陈焕镛澄清。1947年,法院当局迫于民意,以“不予起诉”了结这桩冤案。
据考证,陈焕镛曾先后在广州的康乐村、五山石牌等地建有苗圃,甚至连广西桂林雁山也有他指导布置的植物园(现桂林植物园内)。这都是他“建立一个镇守祖国南大门、作为对外窗口的全国最大植物园”的伟大设想的组成部分。

馆藏银杉标本
身体力行 新兴学派楷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以中山大学农学院等为基础组建的华南农学院从中大独立出来,而植物研究所仍归属于中山大学。直到1953年12月,中科院才与高等教育部及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取得共识,正式接收了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及前岭南大学自然博物馆三个单位,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其广西分所。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护林造林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陈焕镛向广东省申请成立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木园,并于1956年正式接收了广东鼎湖山林场树木园,占地面积约17000亩。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就成了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陈焕镛曾多次带人前往当地林场采集标本。1978年,这里成立研究站,进行数据监测等研究活动,并在1979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单位。此时,陈焕镛已去世数年了。
上世纪60年代,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视察华南植物园曾题词:“必须实事唯求是,壮志雄心不可无;树木固当勤垦难,树人更要费工夫;作风朴素甘艰苦,学派新兴立楷模;改造自然和世界,东风吹送上鹏途。”可以说,这是对陈焕镛等开拓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最好总结。

华南植物园里陈焕镛住过的小楼
【访谈】
他为中国植物学研究打下基础
黄瑞兰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陈焕镛传》(即将出版)作者
羊城晚报:陈焕镛的植物研究工作对中国植物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黄瑞兰:陈焕镛是中国第一批植物学家,在他之前,中国的植物研究都是被国外垄断的,他带回来很多先进的方法与理念。现在的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依然是中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而我们的植物标本分类,还在沿用他当年那一套植物标本分类系统。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贡献卓越,他成为第一批中科院院士,还连续担任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以及他的各种努力下,1956年又成功申请成立了第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工作。
羊城晚报:陈焕镛的名字居然与那么多植物有关联,他对现代植物研究的影响有多大?
黄瑞兰:他创办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华南植物园的前身。研究所逐步转型成一个综合科学研究机构,而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努力为今天我们的植物学研究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陈焕镛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植物研究。他组织编写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还担任《中国植物志》第一任主编。他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植物研究人才,包括我国蕨类植物研究“开山鼻祖”秦仁昌,有“中国植物园之父”美誉的陈封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张肇骞、蒋英等。
羊城晚报:目前华南植物园研究工作的传承、进展如何?
黄瑞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焕镛便开始尝试把华南植物研究所向成为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拥有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植物研究机构推动发展。现在,在全世界的植物园综合实力排名中,华南植物园已位列前五。
遥想1919年,陈焕镛前辈回国,立志为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要让中国摆脱当年的困境,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我们也希望他这种爱国、爱科学、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研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
【延伸】
属于植物学家的特别“致敬”
陈焕镛一生中与许多同行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得到过不少国际友人的帮助,比如他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时的恩师杰克教授,以及美国农业部派驻菲律宾的植物学家、比陈焕镛年长14岁的梅尔教授等。
1934年,梅尔在写给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想致敬或感谢某人对你的帮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植物新种命名里。”有趣的是,陈焕镛及他的朋友们真的将这个建议充分实施起来,这见证了中国植物学研究建立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这些植物学家们发表的不少新种植物名中,都出现了彼此的名字——其中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物新属就有4个(分别由德国植物学家巴瑞德和中国植物学家蒋英、张宏达、刘玉壶定名发表),植物新种有44个。而在陈焕镛发表的新种中,嵌入的人名超过40个,这些人大多是和陈焕镛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植物学界同仁或是他器重的学生,包括16名国外学者。
1941年,陈焕镛和蒋英联合发表海南物种新属——萝藦科的梅乐藤属及驼峰藤。陈焕镛特别在文章里写道:“敬献给梅尔,以答谢他对本文两位作者所代表的两代中国植物学工作者的帮助。”
发表于1925年的长叶榧,是陈焕镛献给杰克教授的;1963年陈焕镛鉴定并定名的木兰科新属观光木属,是为了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的;以胡先骕的姓氏命名了植物新种胡氏栎、胡氏芮德木,也见证了陈胡二人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
此外,陈焕镛1927年发表的秦氏紫荆,嵌入了他的学生秦仁昌的姓氏;而1929年,秦仁昌发表新种陈氏耳蕨,也特意在中英文名字中嵌入了陈焕镛的姓氏。在陈焕镛发表的植物新种中,他最器重的弟子侯宽昭的名字出现多达15次。
跨越国界、跨越时空,一个个植物拉丁学名,见证了植物学家们不朽的友谊。
(感谢华南植物园对本文采写的大力支持)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68efc7ff-25b6-49ae-9d66-a48eccc33570.png)



6f188dc8-cc77-4e0a-9c78-4e6ba1408084.jpg)
6ae75a70-2704-4398-806c-1a7802ab0a4b.jpg)
5923cad0-3c98-4493-be8a-d1715eaaa48c.jpg)
880ceeb0-d937-4563-96b7-7f669b9ce00f.jpg)



9d8b28c0-67d3-4352-a36d-d9194a705316.jpg)